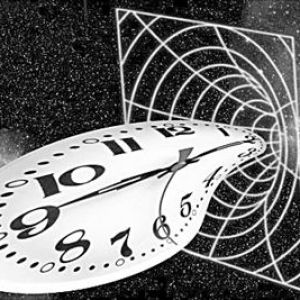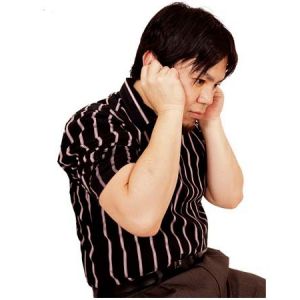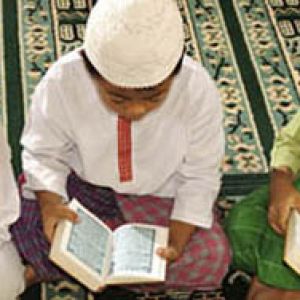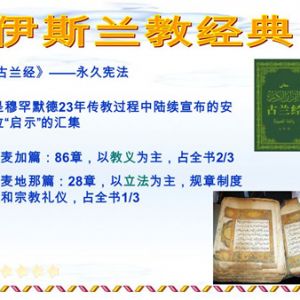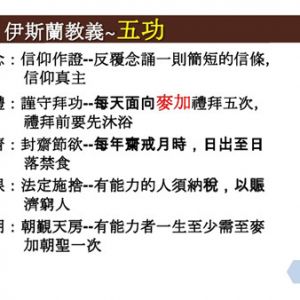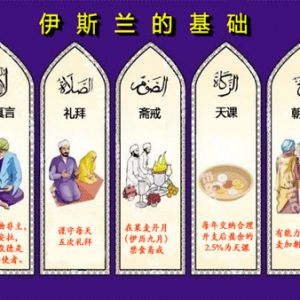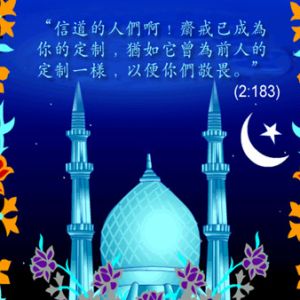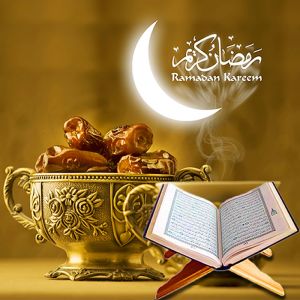《理解圣史》前言(三)
上一篇推文中,布推长老简述了圣史著述中“现代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史,说明了它的基本特征。今天的推文,旨在说明该流派的现状、分析其中存在的悖论、揭示其以科学之名“反科学”的事实,并说明进行圣史研究应有的态度和方法。
《理解圣史》前言
(三)
拉玛丹·布推 著
该流派的现状【1】
该流派在圣史著述和理解方面所获得的重视,以及它的拥护者不知从哪天起开始流露出的热情,实际上只是历史进程中的一段必经之路,故这些人也情有可原。
长期闭目塞听之后,他们睁开眼睛突然就被欧洲科学复兴的强光照射,第一眼自然头晕目眩,看不见事物的真相,无法细加辨认。要过上一段时间,等眼睛习惯了强光照射,许多事情便能分辨,真相便能彰显无遗,一清二楚。
今天,上述种种已为陈迹,蔽眼之物已然消失,文明自觉的这一代,视力已经恢复,他们开始认真对待“科学”的真相和实质。而之前的那些人,仅仅抓住了“科学”的标签,被一些口号蒙蔽,之后才迷途知返,受惠于专业的研究者和自由的思想家们的远见卓识,开始相信所谓的反常与奇迹,实际上并不违背科学真理及其标准。
因为所谓的“反常”,不过是违反了人类所知的常识,但常识和习惯并不能成为判断一件事可能与否的依据。只有人类常识熟知之事才可能发生,人类常识未解之事便不会出现,科学何时做出过如此的断言?
今天,每一个研究者和有文化的人都知道,对此问题,科学家们的努力所获致的最新的结论是:我们所能看到的事物间的因果关系,并非一种固有的联系,它尚待分析与解释,然后归纳出存在于关系的表象之下的规律,不可反其道而行之。
关于反常之事和奇迹,你若求教于科学的规律,根据所有科学家借助当代的科学文化而达到的认知现状,它会告诉你:“反常和奇迹并不属于我的专业和我的研究领域,我无权判断它。但是,若它在我的眼前发生了,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成为了一个研究对象,等待观察、分析、论述和解释,然后,这种反常的表象之下的规律会被揭示”。
曾经,部分科学家认为自然界中“因”与“果”的关系是一种不可抗拒、亘古不变的必然的关系。但那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穆斯林学者们(特别是伊玛目安萨里)不断提醒和捍卫的真理已经获胜:“因”与“果”的关系,仅仅是二者的连结而已,此外无他。科学的定律和法则,只是对这种连结的一种解释。至于这种连结背后的秘密,那是属于清高的安拉的知识,他赋予每一件事物相应的属性,并加以引导。
我们已经看到经验主义哲学家大卫·休谟是如何通过犀利清晰的论述呈现这一真相。【2】
是的,对于每一个尊重理性和真相的人而言,接受任何一则圣训——不管它是否符合常规——只需要确认一个条件:他获取这则圣训的渠道是否科学合理,即确认信息的传播过程是否符合传述、传述线索和人物鉴别学的要求。这种科学的衡量标准,对其进行详细的论述需要很长的篇幅,此处暂不赘述。
侯赛因·海卡尔在其《穆罕默德生平》中说:“我没有采纳圣史和圣训中记录的任何东西,因为我更愿意以科学的方式进行这项研究。”像他一样说出这种话的人,必定会让今天的科学工作者们无比惊讶。
他的意思是让你放心,为了保护科学的尊严,他甚至没有采纳《布哈里》和《穆斯林》中所确定的任何东西。伊玛目布哈里依照那些精妙绝伦的条件所传述的一切,更像是严谨的科学工作,能够保证一言一语的传述都经过严苛的、科学的筛选。与此相对,那些基于猜想和臆测的方法居然是对科学的尊重和对科学规则的坚守!这岂不是科学遭遇的最可悲的灾难?
如何按照我们所说的方法研究圣史?
众所周知,当穆罕默德出现在阿拉伯半岛上时,他向全世界宣布他是安拉派遣给全人类的先知和使者,以便确证之前的众先知带来的真理,以便让人类承担起众先知曾让他们的民众所承担的各种责任。并且,他说明他是最后的先知,是历史上环环相扣的先知链上的最后一环。然后他进一步阐明了他的身份:他是一个凡人,只不过他兼具了人类一切高贵的德性。但是,安拉通过启示将使命托付于他,让他向人类传达,使他们认识自身真正的实质,为他们标示出今世生活在神圣之国的地图上的坐标,让他们知道死后必将抵达的归宿。同样,也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实质决定了他们必须行为自主,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凭借对安拉的坚信和自主的选择成为安拉的仆人。同时也提醒他们,他们的仆人身份实则是一种无法回避的现实。对于其奉命向全人类传达的使命,他强调自己无权在其中增减或更改丝毫,而安拉的言辞也肯定了这一事实:
“假如他借我的名义捏造谣言,我必以权力逮捕他,然后必割断他的大动脉,你们中没有一个人能保卫他。”(69:44-47)
穆罕默德没有向世界宣称他是一名政治领袖、国家领导、思想家或革命者,整个一生,他都不曾按照他个人的想法擅自行动。
既然如此,当我们想要研究他的生平时,合乎逻辑的方式便是:从其本质身份的角度——那是他向全世界所宣布的——来观察他的言行是否一致。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研究他作为人类个体在其生平中呈现的所有面向,但前提是我们必须以客观、科学的证据为火炬,烛照隐藏在其本质身份中的真谛。
“我们不必按照穆圣所希望的方式来思考、理解其圣品和使命的意义”。是的,如果一切与我们的结局无关,如果穆圣与我们的自由和行动毫无瓜葛,如此宣称或许我们也能接受。
但是这个问题与我们自身息息相关,它为我们揭示我们的认知和行为中的种种义务,如果不能一一实践这些义务,我们必将陷入非常可悲的结局。这个问题过于重大,容不得我们认为其与自身无关,也容不得我们对其避而不见。
避开穆圣为自己定义的本质身份,却娱乐化地去思考他作为人类个体的其他面向——而那与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与他的本质身份也没有任何关联——明显是一种逃避。
这个人——穆罕默德——站在我们面前,向我们表明他的实质,坚信不疑且满怀深情地提醒我们:“指安拉发誓,你们必将死去如同沉睡,你们必将复活如同苏醒,指安拉发誓,天堂是永恒的,火狱也是永恒的,”然而我们不重视他本人和他的话,却转而去关注他的天才、雄辩和睿智。最大的逃避莫过于此。
难道不是吗?假如你走到一个岔路口,有人向你走来,为你指出可平安通行之路,警告你别误入险象环生的歧途。你不去注意他对你说的话,却转而去注意他的容貌、衣服的颜色和他说话的方式,并将这视为一种教诲和指导而沉迷其中,这种举动是否合理?
我们的初衷决定了我们要研究我们的领袖穆罕默德生命中的方方面面:他的成长和他的美德、他的个人和家庭生活、他的坚忍和奋斗、他的交友和对敌、他对红尘浮生的态度等等。而且,这应当是一种客观、诚恳而细致的研究,以科学的方法为指导——这种方法的基础便是圣训的传述、传述线索及圣训健全的诸条件。
我们的初衷决定了要研究所有这一切,但条件是所选的途径要能够通达研究的目的——证实他的圣品、阐明启示的真谛。以便在客观而不染私心杂念的研究之后,一切得以昭彰,而我们能够明白,他不会私自创制任何教法和例律,他只是忠实地向我们传达,这是众生之主的意志。于是,我们才会留意自己对教法和例律的责任——重视和履行。
仅仅从人的角度研究圣史,并且使其偏离先知自己宣布的本质身份之人,必定会深陷无路可出的迷宫,百思不得其解。他们面对许多谜题时会感到费解。比如波斯罗马坚甲利剑,自古征战不休,霸权不可一世,穆斯林却征服了其文明的要塞和帝国的强权;比如阿拉伯半岛上既不见任何文化的萌芽和也没有任何启蒙教化的学堂,却突然出现了健全的法制为其加冕。这与社会学家的理论要怎样调和?他们认为,一个民族法制健全,显而易见是该民族文化、文明成熟和社会高度发展的结果。可彼时的阿拉伯半岛尚在文明的襁褓中,对学识、文化和复杂的社会生活一窍不通。
对于不考虑先知的圣品之人,这些谜题在唯物的、常规的分析之下纯粹无解。我们看到多少这样的研究者,思想摇摆不定,忽左忽右,只为找到一个解开迷局的突破口,可他们的努力却无济于事。
与此同时,摆脱这种迷茫的出路其实清清楚楚,那便是如我们之前所说,理性客观地研究圣史,把先知自我宣称的本质身份当做研究他整个一生的线索。
这种研究最终会迫使我们坚信他是一位先知,是来自安拉的一位使者,也会促使我们摆脱迷茫并洞悉一切谜题中的奥义:关于其圣品,他诚实无欺,他获得派遣他的主宰之援助是必然的,古兰经是主宰对他的启示,这也是必然的,故这套健全的法制乃是由安拉制定并降示,绝不是出自一个文盲的民族之手笔。
安拉在古兰经中对信士们说:“你们不要灰心,不要忧愁,你们必占优势,如果你们是信道的人”(3:139)“我要把恩典赏赐给大地上受欺负的人,我要以他们为表率,我要以他们为继承者”(28:5)“当时,你们求援于你们的主,他就答应了你们:‘我要陆续降下一千天神去援助你们。’安拉只以这个答复向你们报喜,以便你们的心境因此而安定,援助只是从安拉那里发出的,安拉确是万能的确是至睿的。”(8:9-10)
朦胧者已然清晰,答案已然明了,迷雾已然消散,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因为强大全能的创造者援助了归信他且遵循其指导之人,让他们战胜了他所意欲者。
如果安拉要援助他的使者和那些信道的仆人们,却又没有发生任何奇迹作为支援和援助,那才真是令人费解之事。
注释:
【1】此文的写作时间,是上世纪70年代。
【2】大卫·休谟(1711—1776),苏格兰哲学家。他否认事物之间存在所谓的“因果关系”,取而代之,他提出“恒常连结”的概念,他在《人性论》中写道:“我们无从得知因果之间的关系,只能得知某些事物总是会连结在一起,而这些事物在过去的经验里又是从不曾分开过的。我们并不能看透连结这些事物背后的理性为何,我们只能观察到这些事物本身,并且发现这些事物总是透过一种经常的连结而被我们在想象中归类。”